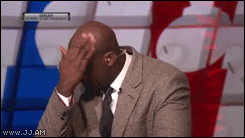《跟他学》2008年
拍完《跟我学》过了大概一年,我觉得之后应该有“你我他”,连起来组成一个世界。8年以后,开始拍《跟他学》。

《跟他学》拍摄幕后
运了20吨的书,从废品收购站收回来,放了一年让它长霉。一年后,又卖给收购站,每吨价格还涨了300块。


《跟你学》2013年
2013年拍了《跟你学》,大概是120个课桌,趴着睡觉的这些人,跟一个打着点滴的老头一起学。老头是我自己扮演的。
当时废品收购站运来的很多工具书、高考教辅书,根本没开封,带着塑料皮。我还截了当时我们湖北当地的新闻,临高考前几天,全班打营养液,亢奋起来复习,不能睡觉。
这样“你我他”算在一起,有10年跨度。它有一个反问:到底我们要跟什么学?

《论坛》出演发言人 2001年

《学前班》扮演老教师 2002年
我拍的绝对都是社会的真实
我七八成作品里都有自己。有时候我作为一个主角,有时候我只是作为一个旁观者,一个教师、一个乞丐、一个老人,几百人的其中一个学生,偷偷地看。

2008年作品《临时病房》:大家坐在一起很麻木地接受治疗,我就像是一个超时空的人,跟他们没有关系,只是在那里看看报纸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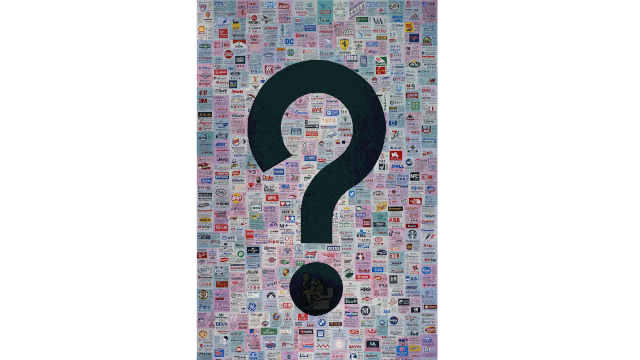
2020年作品《问它》:我全身裹满了泥,坐在一个马桶上,扮演了一个思考者,观众在展厅里要走得离这幅作品很近,才能找到我。
人在看我,我王庆松也在看这个社会。
不管社会发生什么变化,我们既是个参与者,同时可能也是一个怀疑者。“我跟社会的关系”,这一点在我的作品中一直很重要。
早期我总是想把自己放在很英雄,很重要的位置,后面慢慢就去藏自己,把我融入在画面中,尽量不被人发现。


《大摆战场》2004年
我们走到任何地方,铺天盖地的广告,我就做了15米高,大概38米长的一个海报墙,那些牛皮癣啊小广告啊,大概写了一个月,一边看雅典奥运会一边画那些道具。
起名《大摆战场》,一听就是很中国的一个名字,油盐酱醋、针线、老外家教……可以看到整个社会的缩影,各家又互相竞争,整个像一个战场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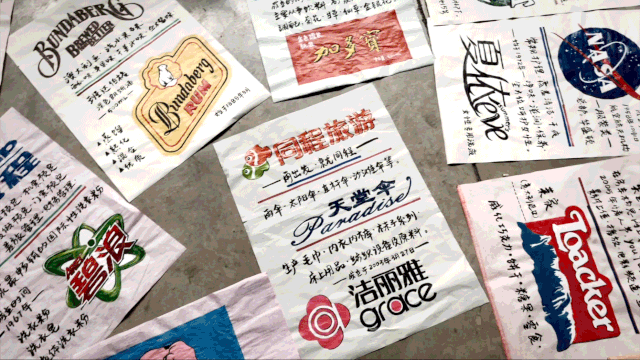

《问它》幕后 2020年
《问它》是今年疫情期间写的,主要是世界500强的LOGO,花了4个多月,每天10个小时,一张张画出来,100度老花镜也成了300度。
过了十几年,我们看到很多商标消失了。商业社会发展到这个程度,其实我们无法摆脱,但我们依然需要给这一切打一个黑色的、正式的、严肃的问号。

王庆松在展览现场
我很少穿戴有商标的东西,物质上需求不多,也不擅长社交场合。别人来看展览,我不知道说什么,“谢谢你来了”。
我来北京就觉得要匍匐前进。能坐起来,我尽量坐小马扎;能站起来,我尽量半弓着腰站。因为你无依无靠。多少年之后,别人说庆松,好像做得还不错。我还是尽量低调,人就是得这么低调地过着。

《问它》拍摄幕后 2020年

王庆松在展览现场
摄影,其实是帮我找到了一种方式,去跟别人交流。
如果按普通的方式拍摄5年,别人可能会用200张、300张照片去呈现,但我就只需要一张照片,把我这么多年的各种社会观察,做成像压缩饼干一样,都锁在一张图片里。可以在里面不停地去“找东西”。
别人总说我的照片,什么艳俗不艳俗我就很烦,什么观念摄影,我根本不是这么想的。
我认为我根本不是摆拍,我拍的绝对都是社会的真实,每个镜头都是在社会中找到的。
它没那么生动,没那么好看,但它就是有一点真实。

王庆松工作室附近的街景
后记:他的发型?村里的生活?......
7月底,在疫情风险降级后,一条终于来到了北京。
沿着机场高速公路下来,费了老大劲登记、问询,我们才被允许进入一片藏在城中村里的艺术社区。
这里,一半是平房,沿街一溜日用杂货铺,紧挨着熟食快餐、理发店;楼上留给外来打工者、剩下不多的留守村民。拐个弯,就是一排整齐划一的艺术家工作区,一栋挨一栋。与野生混杂的村民生活区,形成鲜明对比。
10年来,王庆松就隐于此。

生活里,王庆松常穿着人字拖、顶着一头标志性的“雷电发丝”。他说这发型得有快20年了,他找理发师傅把黑发全剃了,只留下一根根稀疏分布于头顶的白发丝,一撸,发丝就能一根根竖起来。“有时候一进电梯,所有人都想退几步。”他说就喜欢这样让人有点不舒服的感觉。
“老师您有什么爱好?”“最爱睡觉,太爱睡觉了。只想躺着。”这回答,让人联想到2008年他的一幅《跟我学》拍卖出500多万高价时,他本人的反应是:“那天的新闻,就是打扰了我休息,还有七八个电话打进来问我还有没有别的作品。”
他笑称自己是“低端人口”。当我们跟着他出了门,他就像在城中村里隐形了,一晃神就找不到了。
部分图片由王庆松、当代唐人艺术中心提供






 论坛通告:
论坛通告:
 个人空间:
个人空间:

 论坛转跳:
论坛转跳:








 赞
赞  花篮
花篮  投诉
投诉 踩
踩  分享
分享